- 学习新思想
- 十九大时间
- 学习研究
- 红色中国
- 学习科学
- 环球视野
- 习近平文汇
- 学习电视台
- 学习慕课
- 强军兴军
- 学习文化
- 美丽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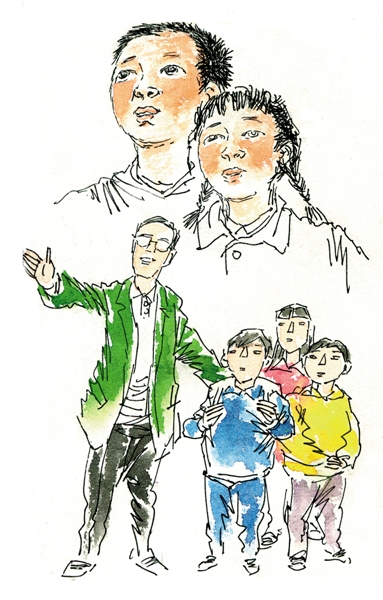
插图 何富成
这是一双双充满期盼的眼睛。这是一双双孤独的眼睛。
他们本是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年龄,却不得不变得成熟、懂事。他们在学校、在孩子堆里,总是落落寡欢,不太合群,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他们有父母,却活得像孤儿。他们有家庭,却少了些温暖。
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做“留守儿童”。
“我还希望一家人能开开心心在一起”
对中宁县宽口井中石油希望学校八年级的小梅来说,假期总是混杂着甜蜜、欢乐、无趣和失望。
今年暑假,外地打工的爸爸、妈妈回来了,一家人团团圆圆、开开心心过了两天。小梅在妈妈身边唧唧喳喳说个不停,一会儿讲学校的事情,一会儿唱刚学会的新歌。然而幸福的日子到第三天就结束了,爸爸启程去天津寻找新的工作,妈妈到红寺堡一家餐馆继续打工,家里又变得和往常一样冷清。
“想爸爸、妈妈吗?”
小梅点点头,想了想,又垂下眼帘,摇摇头,“爸爸、妈妈要工作,很辛苦。”年仅13岁的小脸上,有着超出同龄人的平静和老成。
这5年,父母常年在外,小梅成了小“当家”,里里外外都是自己打理。每天下午放学,她先迅速写完作业,再给弟弟辅导功课。妈妈不在,她尽量把家里打扫干净,被子叠放整齐,屋里虽不是很整洁,但还算井井有条。今年,小梅学会了自己做饭,清炒土豆丝、白菜,她也能做得像模像样。
采访中,邻居奶奶进来,给小梅放了两个白饼子。“娃娃们可怜,爹妈不在,啥都要自己操心!”
“谢谢奶奶,我会自己做饭了。”
“我知道,炒的土豆丝都糊了。”
听到邻居奶奶的话,小梅低下了头,吐了吐舌头。
宽口井村的村民们都是从海原县深山里搬过来的,大部分村民以打工为生,常年外出,几乎家家都有“留守儿童”。
上午放学时分,记者在宽口井中石油希望学校看到,学生们排着队到学校食堂打饭,拿到班里吃完再排队回家。“我们学校享受国家免费早餐和午餐政策,只要在上学期间,孩子们吃饭就不用愁。”宽口井中石油希望学校校长万占文说,“每个学生5.5元的用餐标准,早餐有鸡蛋,午餐有肉。家里没大人的孩子,趁着中午在学校免费吃饭,吃得饱饱的,晚上基本就不用吃了。”
而在没有免费午餐的时候,孩子们的生活压力大了很多。
“节假日你都做什么?”
“周末做做家务,自己洗衣服什么的,有时候学校会安排补课。”
“寒假有什么安排?”
“不知道……可能我会去爷爷奶奶家吧,这样吃饭不用发愁了。”一提起假期,小梅就一脸的失落。
“新年有什么愿望?”
“好好学习,长大了报答爸爸、妈妈。”小梅回答得很“官方”。她懂得父母奔波打工的艰辛,她也知道,只有成绩好才能让父母开心。
“我还希望一家人能开开心心在一起。”她想了想,小声补充道。那双懂事的眼睛里,闪烁着深深的渴望。
“我已经不记得他们的样子了”
银川市西夏区兴泾镇西干村的小虎,父母也不在身边。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的小虎,虽然比小梅多了两位长辈的照顾和疼爱,但他并不快乐。
当记者来到小虎家里,65岁的马卉兰正在给孙子洗球鞋,一双裂满疮口的双手冻得通红。“娃儿长得快,鞋子已经穿不上了,我把他哥哥的鞋子找了出来,洗洗让他穿。”马卉兰一边跟记者说,一边拿手比画着:“上七年级了,肯长个儿,中午吃了3个大酸菜包子,还说没吃饱。”
小虎的父母长年在外打工,在他三岁的时候,父母离异,母亲就再没回来过,从那以后,父亲也很少回家了。小虎的生活起居全靠爷爷奶奶照顾。马卉兰身体不太好,几天前的一个中午,她正在厨房给小虎做饭,突然昏倒在地。当时老伴儿出门办事,家里再无其他人,马卉兰只能静静躺在地上,等清醒了些,才慢慢爬了起来。
“我给老伴说,要是我就这么走了,这娃儿就没人管了。”马卉兰说着,忍不住擦拭眼角的泪花。“以前他可调皮了,老跟人打架,现在懂事多了,听老师说,学习也肯上心了。”提起孙子的学习,老人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这个年满13岁的少年个头已经蹿到了1.67米,但那张稚嫩的小脸上,既没有同龄人的活泼和朝气,也没有大人的成熟和淡定。当有人问他时,他显得非常腼腆、内向,话极少,大部分时候只是点点头或摇摇头表示回答。
马卉兰说,这几年,小虎父亲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有时候半年见不上一次面,回来时父子俩也很少交流。小虎常年见不到父亲,见了面反而会躲着走,并不愿意和父亲亲近。
“寒暑假和周末,你喜欢做什么?”
“村上安排了老师给孩子补课,假期每天都上课呢。”爷爷抢着说。
“那你学习成绩在班里能排第几?”
小虎低着头不吭声。“娃心里不痛快,没有爸爸妈妈照顾,胆子小得很,在学校里也不敢跟人说话。”奶奶补充说。
“如果有一天爸爸妈妈回来,你想跟他们说什么?”
小虎摇摇头,眼睛里全是漠然,半晌说了一句:“我已经不记得他们的样子了。”
关爱留守儿童需全社会共同发力
不是所有留守儿童的眼睛里都充满忧郁和悲伤。
大家都说,小雅现在开朗活泼多了。小雅的父亲去世了,母亲改嫁后就去外地打工,留下她跟爷爷奶奶相依为命。在学校里,她是最沉默的那一个,无论上课还是下课,都不爱说话,甚至不敢跟人拍照合影。
2016年,一个叫“六盘善行”的社工组织走进了她的生活。
“孩子很敏感,害怕得到关注,有点自卑;学习自觉性很差,但在运动方面特长突出。”在宁夏六盘善行社工服务中心对留守儿童的个案工作计划手册里,详细记录着小雅的生活状况、个性特征,并针对性地提出帮扶方案:引入志愿者入户走访,在周末一对一辅导功课,组织小雅参与“奔跑吧兄弟”“盲行”等活动,增强其集体归属感、获得感和被尊重的需要,鼓励她表达自己的想法,培养自己的爱好。
“小雅性格温柔又非常善良,是个很听话的孩子,在我们的鼓励下,她现在能积极主动参加集体活动,还敢大胆发言,变化非常明显。”社工史文静说。
“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过过生日,今天让我非常难忘。”2017年8月22日,在宁夏六盘善行社工服务中心和西干村村委会联合为留守儿童精心策划的一场集体生日晚会上,小雅激动地说。那天,她和大家一起唱生日歌、吹蜡烛、吃蛋糕,开心地享受生日的喜悦和来自朋友的祝福。
永宁县闽宁镇福宁村的红红,怯生生的眼睛里开始充满自信。“爸爸,你和妈妈在那边冷不冷?吃得好不好?你们在那边不要省钱,冬天天冷不要吃凉饭。”“爷爷奶奶身体都好,你们放心。”周末,在福宁村村委会“妇女儿童之家”的电脑前,14岁的红红和远在内蒙古打工的爸爸通视频电话,口吻像个小大人。
这两年来,红红变得爱笑了,在村委会的“妇女儿童之家”,她不仅能及时跟爸爸妈妈取得联系,每周六,还有志愿者老师教他们唱歌、跳舞、做手工,生活丰富了很多。“没有父母陪伴的童年孤独寂寞,我们开通‘亲情热线’让留守儿童能及时和父母打视频电话沟通,请我们这里的向日葵志愿服务队每周末组织活动,还定期跟孩子的监护人、学校沟通,从生活、学习、人身安全保障等方面对他们给予关爱,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父母和社会的温暖。”福宁村留守儿童督导员何婷说。
2016年,银川市在6个村子建立起“儿童之家”,通过与社工组织、志愿者服务队合作,尝试解决留守儿童问题。
2017年,自治区将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纳入政府民生实事,投入1000万元在农村社区建设了200个“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打造集“学习娱乐、成长教育、维权帮困、安全保障、亲情培育”为一体的关爱保护阵地。
今年,我区全面推进“儿童之家”建设,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儿童之家”1389个;自治区政府出资800多万元,为全区2242个行政村各配备了一名“三留守”关爱行动督导员,有效解决了关爱留守儿童“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社区各界共同发力。”自治区民政厅社会事务处武俊华告诉记者,财政、民政、团委、妇联各部门携手,运用“儿童之家”平台,积极链接社会资源,引进专业社会组织开展留守儿童关爱服务,齐心协力为他们的学习成长创造一个快乐幸福的社区共享家园。
目前,我区4071名农村留守儿童,通过各级组织的帮助得到了有效监护,没有一个孩子辍学、失学;其中706个家庭经济困难的孩子,被民政部门及其他社会救助部门纳入了保障范围。( 尚陵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