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新鲜出炉的著作,是鲁人勇用三十多年的时间,实地考察诸多线路,搜集整理大量史料而得出的成果。洋洋洒洒近30万字,既有对宁夏各时期丝路走向的考证,也有对中外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交流的描述。其中的大部分内容,是我们过去闻所未闻的。
丝路上曾被人遗忘的角落
《宁夏:丝绸之路的门户》,是鲁人勇对自己三十多年研究的一个精准总结。
1960年8月,从交通部重庆航务工程学校毕业的鲁人勇被分配至原宁夏航运公司工作。1981年,机缘巧合,鲁人勇参加了《宁夏公路交通史》的编修工作。当时此书并没有编写丝绸之路的任务,只要求将宁夏古代交通作为背景资料融入书中。然而,在搜集工作进行一年多后,他惊奇地发现:对丝绸之路的研究,宁夏竟无人涉足,连一篇“豆腐块文章”也没有;查遍全国写丝路的专著、论文,也都只字不提宁夏。可是,“在我所见的资料中,有一批十分珍贵的证据,可以证明丝绸之路不但经过宁夏,甚至在唐末至宋初,还是东段丝路唯一可用的主线。”鲁人勇暗暗下定决心,不能让宁夏段丝路,继续处于“被人遗忘的角落”。
此后,怀着对丝绸之路宁夏段一探究竟的心情,鲁人勇一直将其作为重点研究方向,繁忙工作之余,他沉浸在古籍史料的搜集整理之中无暇他顾。
一步一个脚印走在“丝路”上
《宁夏:丝绸之路的门户》并不是鲁人勇的第一本著作。
1983年2月,鲁人勇的第一篇论文在《宁夏社会科学》发表,标题就叫《宁夏境内的丝绸之路》,正是这篇文章,让他成为宁夏段丝路研究的开拓者。次年,他又完成论文《唐末五代至北宋的丝路主线——灵州西域道考略》,在《中国公路交通史研究》发表。1988年出版发行的《宁夏交通史》,全书25万字,约五分之一是写丝绸之路。
1989年,鲁人勇调至宁夏交通厅办公室。繁忙的工作并没有阻挡住他的热情,利用休息时间,他拿出过去搜集的资料继续研究。十年间,他利用出差、开会中转等票的时间,到国家图书馆查阅古籍。坐汽车出差就实地看路,跑遍了陕、甘、宁、青,走过很多古道,考察过大量古遗址,而且都做了记录。正因为有这个优势,在写路之前,已经是“心中有路”。
1989年后,鲁人勇又出版了《塞上丝路》一书。1993年,台湾复汉出版社将此书版权购去,改书名为《丝绸之路宁夏段揽胜》,在台湾地区发行。
1995年—2000年间,鲁人勇兼任《中国丝绸之路交通史》的副主编,将宁夏段丝路的基本内容编写进该书之中。此后,中国丝绸之路只包括陕、甘、宁、青、新、豫,即沿于此。
时间来到了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随后,党中央又提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部署。听闻此消息,鲁人勇觉得新书中应该增加宁夏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丝路旅游等内容。“纵观历史,丝绸之路的走向和选线,是两千多年无数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分析宁夏各时期的丝路主线,都有两大特点:一是最捷径,二是最好走。这些线路,今天仍是交通主干线所经。因此,在今后的交通规划中,应当充分借鉴古人的实践成果。”
在鲁人勇这位“老交通”人眼中,宁夏的新丝路经济带建设,交通要先行,尽快建成通疆达海、连接亚欧、多种运输方式并举的高效综合运输网,让宁夏,这个丝绸之路的门户,发挥更新更大的作用。
这是本值得一看的历史书
2001年,退休之后的鲁人勇终于有时间重新审视这些年来对宁夏段丝路的研究成果。“过去的丝路研究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比如只重路线考证,轻商贸往来,忽略文化交流。通过这十多年的探究,我又产生了一些全新的观念,如:唐代参天可汗道路出灵州,是重要的草原丝路;西夏并未中断丝路交通,但有变化;元代的黄河水驿,打通了便捷的河套丝路。对商贸往来、文化交流,则开拓视野,从头搜集资料……这些,在新书中都有所体现。”
知识性、趣味性、严谨性,一个也不能少——这是鲁人勇对新书的自我评价。他在编写《宁夏:丝绸之路的门户》的最初就有一个想法——不仅要写得专业,更要能吸引普通读者的眼球。为此,他加入了许多既有趣,又有史料可以佐证的小故事。“比如,北魏成书的《洛阳偏蓝记》详细记录了波斯‘胡王’派使团送狮子到魏都洛阳的经过:路经固原时,被农民起义军领袖万俟丑奴扣留,取其吉祥之意,自称天子,改元‘神兽’,与魏朝廷分庭抗礼。这头狮子作为传播友谊的使者,在固原生活两年多,见证了‘百国千城,莫不款附;胡商贩客,日奔塞下’的丝路盛况。又比如:在吐蕃攻陷渭水流域和六盘山区后,丝路主线中断了90年。突然有一天,唐朝派往于阆的使节,于阆派往长安的使团,在灵州城不期而遇。这说明新的丝路主线——灵州西域道,已经辟通。”鲁人勇说,诸如此类的史料在书中比比皆是,他真心希望每个读过此书的人,都能有所收获。(记者 李晓睿 文/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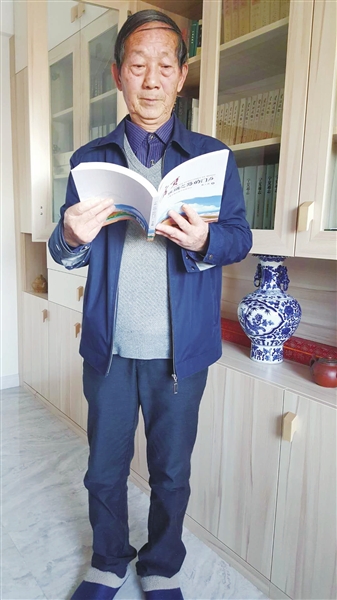
鲁人勇近照。
